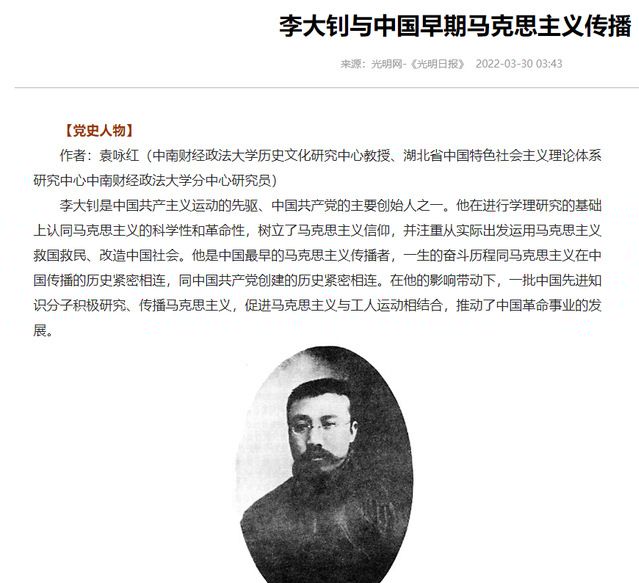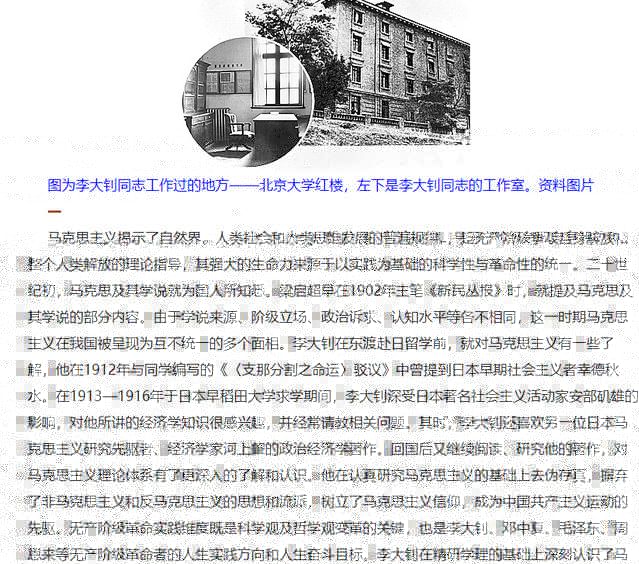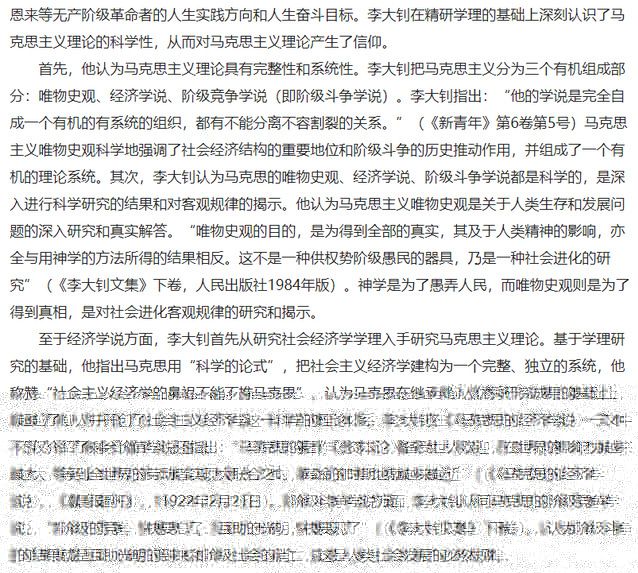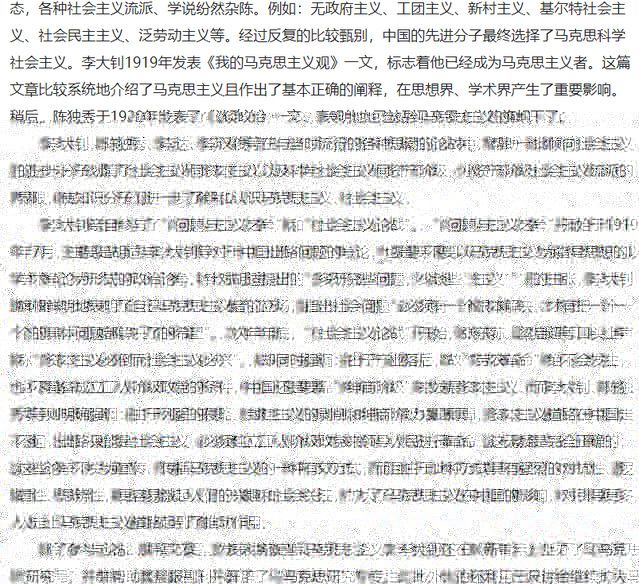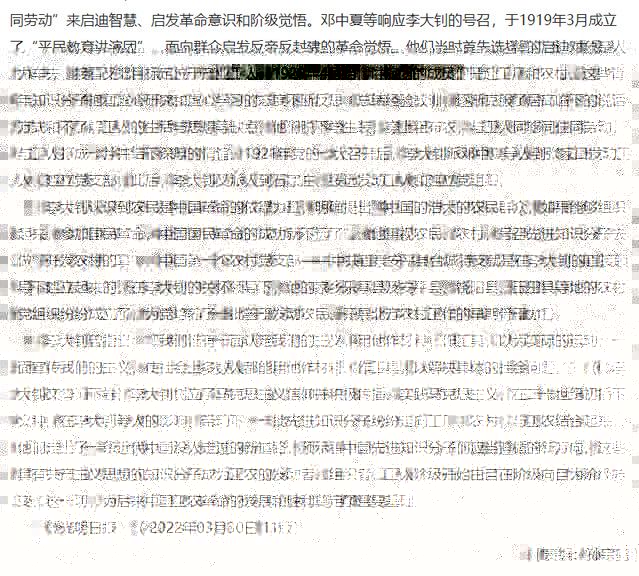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教授袁詠紅于2022年3月30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刊登全文如下:
李大钊是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在進行學理研究的基礎上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革命性,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并注重從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救國救民、改造中國社會。他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一生的奮鬥曆程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曆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産黨創建的曆史緊密相連。在他的影響帶動下,一批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積極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
一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是無産階級争取自身解放和整個人類解放的理論指導,其強大的生命力來源于以實踐為基礎的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二十世紀初,馬克思及其學說就為國人所知悉。梁啟超早在1902年主筆《新民叢報》時,就提及馬克思及其學說的部分内容。由于學說來源、階級立場、政治訴求、認知水平等各不相同,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我國被呈現為互不統一的多個面相。李大钊在東渡赴日留學前,就對馬克思主義有一些了解,他在1912年與同學編寫的《〈支那分割之命運〉駁議》中曾提到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在1913—1916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期間,李大钊深受日本著名社會主義活動家安部矶雄的影響,對他所講的經濟學知識很感興趣,并經常請教相關問題。其時,李大钊還喜歡另一位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先驅者、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回國後又繼續閱讀、研究他的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他在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去僞存真,摒棄了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流派,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成為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無産階級革命實踐維度既是科學觀及哲學觀變革的關鍵,也是李大钊、鄧中夏、毛澤東、周恩來等無産階級革命者的人生實踐方向和人生奮鬥目标。李大钊在精研學理的基礎上深刻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産生了信仰。
首先,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完整性和系統性。李大钊把馬克思主義分為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唯物史觀、經濟學說、階級競争學說(即階級鬥争學說)。李大钊指出:“他的學說是完全自成一個有機的有系統的組織,都有不能分離不容割裂的關系。”(《新青年》第6卷第5号)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科學地強調了社會經濟結構的重要地位和階級鬥争的曆史推動作用,并組成了一個有機的理論系統。其次,李大钊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階級鬥争學說都是科學的,是深入進行科學研究的結果和對客觀規律的揭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關于人類生存和發展問題的深入研究和真實解答。“唯物史觀的目的,是為得到全部的真實,其及于人類精神的影響,亦全與用神學的方法所得的結果相反。這不是一種供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種社會進化的研究”(《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神學是為了愚弄人民,而唯物史觀則是為了得到真相,是對社會進化客觀規律的研究和揭示。
至于經濟學說方面,李大钊首先從研究社會經濟學學理入手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基于學理研究的基礎,他指出馬克思用“科學的論式”,把社會主義經濟學建構為一個完整、獨立的系統,他稱贊“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不能不推馬克思”,認為馬克思在繼承前人優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超越了前人并開創了社會主義經濟學這一科學的理論體系。李大钊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文中不僅介紹了剩餘價值學說還指出:“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備受世人歡迎,在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等到全世界的勞動者實現大聯合之時,革命的時期也就越來越近”(《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晨報副刊》,1922年2月21日)。階級鬥争學說方面,李大钊認同馬克思的階級競争學說,“階級的競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現了”(《李大钊文集》下卷),認為階級鬥争的結果就是互助光明的到來和階級社會的消亡,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科學理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經得起任何質疑、攻擊和時間的檢驗。李大钊在精研馬克思主義學理的過程中,始終秉持着一位嚴謹學者應具有的審慎的、科學的态度,不斷地進行獨立思考和驗證。他認為不能将馬克思主義當作盲目崇拜的偶像和教條,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并将随着世界人民的實踐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
二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李大钊在北洋軍閥的恐怖統治下熱情讴歌十月革命,稱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他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十幾篇文章和講演,歌頌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他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1918年11月)中寫道:“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将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文集》上卷)李大钊認為布爾什維主義的旗幟必将飄揚在全世界,宣告馬克思主義是“拯救中國的導星”,樹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和堅定的共産主義信仰。
當時,以李大钊為代表的愛國先進知識分子從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認為隻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使中國人民擺脫被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厄運。十月革命推動中國先進分子們從愛國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首先,十月革命給予中國人的一個啟示是,中國國情與俄國同樣都是封建壓迫嚴重且經濟文化落後,故也應使用“革命的社會主義”。其次,社會主義俄國号召反帝并平等以待中國,使先進知識分子産生了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再次,十月革命也給予中國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即廣泛發動廣大的工農群衆。這樣,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思想界,就産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開始成為一股相當有影響力的思想潮流。但是,當時許多人對于社會主義還隻是處在一種朦胧向往的狀态,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學說紛然雜陳。例如: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泛勞動主義等。經過反複的比較甄别,中國的先進分子最終選擇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李大钊1919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标志着他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篇文章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且作出了基本正确的闡釋,在思想界、學術界産生了重要影響。稍後,陳獨秀于1920年發表了《談政治》一文,表明他也已站到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了。
李大钊、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在與當時流行的各種思潮的論戰中,幫助一批傾向社會主義的進步分子劃清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以及科學社會主義同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使知識分子們進一步了解和認識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
李大钊親自參與了“問題與主義之争”和“社會主義論戰”。“問題與主義之争”開始于1919年7月,主要是胡适與李大钊等對于中國出路問題的争論,也是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以學術争論為形式的政治論争。針對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李大钊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指出社會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次年年底,“社會主義論戰”開始,張東荪、梁啟超等口頭上聲稱“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卻同時強調:由于産業落後,故“勞農革命”絕不會發生,也不具備成立工人階級政黨的條件,中國還是要靠“紳商階級”來發展資本主義。而李大钊、陳獨秀等則明确強調:由于列強的侵略、封建主義的剝削和紳商階級力量薄弱,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出路隻能是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工人階級政黨來領導人民進行革命。這無疑是完全正确的,這些論争不失為宣傳、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有效方式,而且由于此種方式具有強烈的對抗性、邏輯性、思辨性,更容易激起人們的興趣和社會關注,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對引導更多人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起到了推動作用。
除了參與論戰、撰寫文章、發表講演宣傳馬克思主義,李大钊還在《新青年》上辦了“馬克思研究号”,并幫助《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此外,他還利用三尺講台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馬克思主義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影響力。他1920年便在北大開設了教授馬克思主義的課程“唯物史觀”,随後,又開設了“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将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五四時期李大钊是青年們的領路人,在早期中國共産黨人心目中是精神領袖,毛澤東視他為“真正的老師”。李大钊和毛澤東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共事過,其間,李大钊指導他閱讀了一些關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著作,并保持着交往。毛澤東後來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回顧了他與李大钊的情誼。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學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設有一個小型圖書館“亢慕義齋”(德文Kommunismus音譯),即:共産主義室。研究會的宗旨為“以研究關于馬克斯派的著述為目的”。李大钊組織研究會的會員們搜集和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等人的著作。研究會不僅邀請教授方家來講座,也走進民衆中去宣講馬克思主義。鄧中夏、高君宇等具有共産主義思想的青年學生們聚集在此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黨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由于李大钊在中國最早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且和陳獨秀一起“相約建黨”,因此,在思想界享有“南陳北李”的崇高聲譽。
三
李大钊注意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傳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後,就主張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開始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的“實境”相結合。李大钊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肯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具有普遍意義。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着他的實境”(《李大钊文集》下卷)。
李大钊認為,當人們以一種理論作工具來改造社會時,這種理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适應環境的變化”,即認為理論乃是在運用中得到發展。他強調,“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衆的先驅”,号召“把三五文人的運動”變成“勞工階級的運動”。通過與勞工群衆的“共同勞動”來啟迪智慧、啟發革命意識和階級覺悟。鄧中夏等響應李大钊的号召,于1919年3月成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面向群衆啟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覺悟。他們當時首先選擇的啟迪對象是人力車夫,接着又把目标定位于産業工人。1920年4月始,講演團的成員們開赴工廠和農村。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抱着虛心研究和虛心學習的态度不斷反思、總結經驗教訓,逐漸克服了居高臨下的說話方式和不了解工人的生活與思想等缺點。他們脫下學生裝,穿上粗布衣,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與工人打成一片并結下深厚的情誼。1921年黨的一大召開後,李大钊派鄧中夏等人到張家口發動工人、建立黨支部。此後,李大钊又派人到石家莊、綏遠發動工人和建立黨組織。
李大钊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明确提出“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衆,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他重視農民、農村,号召先進知識分子去做“開發農村的事”。中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中共直隸安平縣台城特支就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在李大钊的關懷領導下,他的家鄉樂亭縣及安平縣、饒陽縣、玉田縣等地的農村黨組織紛紛成立了,為黨培養了一批善于發動農民、開展北方農村工作的早期骨幹力量。
李大钊曾指出:“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李大钊文集》下卷)李大钊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并積極傳播、實踐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播下火種。在李大钊等人的影響、帶動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紛紛走向工廠、農村,與工農結合起來,他們走上了一條近代中國沒人走過的新道路,預示着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們應當遵循的新方向。這些具有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成為工農的發動者、組織者,工人階級開始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變。這一切,為後來中國工農革命的發展和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原文鍊接:https://news.gmw.cn/2022-03/30/content_35621581.htm
原文圖片: